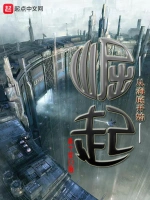訾奶娇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给岑银子打越洋电话。电话铃响了很久,没有人接。她有些失望,她的心情是那样迫切,想把今天的发生的一切告诉好友,想从好友那里得到支持和鼓励。再拨一遍,还是没人接。訾奶娇正想把电话搁下去放水洗澡的时候,收到他传来的简讯。
“明晚来看你。”
只有五个字,她念了整整五遍。
稍晚,訾奶娇终于打通了岑银子的电话。她很有演说家的天分,叙述的时候声情并茂,充分抒发着自己的情感以求引发共鸣。
“奶娇,你快量量体温,看是不是发烧了。”
电话那头岑银子说。虽然訾奶娇看不见她的脸,可银子揶揄的表情还是生动地浮现在她眼前。她也不放在心上,继续跟好友分享她的喜悦。
“他条件这么优秀,难道没有女朋友吗?有过几次恋情你问了没?家里基本情况你都了解吗?”
虽然两人同岁,但岑银子开窍比訾奶娇早,总笑她天真幼稚,担心她受到伤害。岑银子提的问题訾奶娇都回答不了,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压根没关心过这些。
“那怎么行呢?就算其他的不问,他的感情经历你总要弄清楚吧?按照他的岁数,他的条件,怎么也该有女朋友或者根本就已婚了。你别稀里糊涂一头栽进去啊。”
岑银子的话让訾奶娇发热的脑袋瞬间清醒不少,她不得不承认好友的顾虑都有道理。清清白白一个女孩,不能稀里糊涂地扎狗血里,惹一身腥气。
“这样爸爸妈妈会不开心的吧。”
她自言自语道,转而望向窗外的夜空,心情像坐上了升降机,一直往下沉。她顿时沮丧起来。每当她想念养父母的时候,总喜欢在夜里抬头仰望天空,让眼睛去极远处寻找,以为目之所及的璀璨繁星里,必定有两颗星为她而闪亮。那是养父母仍然存在的证明,那不灭的辉光永远守护着她的安宁。
她是个极敏感脆弱的人,情绪变幻像那没来由的风,忽起忽落的。白天她的心在几万英尺的高空飞翔,到了空无一人的夜晚又骤降。
“l'm a big big girl ……”
楼下传来五音不全的歌声,紧接着是开门上楼的声音。这是与她同住的花椒约会回来了。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?一大早就跑了,也不跟我说一声。你跑哪儿去了?”
花椒一见訾奶娇就质问她,脱掉的外套也不好好挂上,随手一扔就赶紧钻进了被炉里,脚不停蹬着訾奶娇的腿。花椒的两腮又红又鼓,火龙果色的口红模糊一片,一看就被人用力吻过了。
“你还好意思问我?自己还不是约会了一整天。老实说,你俩干什么了?”
訾奶娇不怀好意地盯着她笑。
“我先问的你,该你先说。”
两个小伙伴你来我往地算计着,但最终还是就双方的一日恋情做了充分的交流。
“我的天,奇遇啊!看来你注定是要和他好的。别犹豫了,把你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恋爱中去吧!我百分百支持你。”
在訾奶娇眼里,花椒是个对待感情非常勇敢和积极的人,也可以理解为冲动和无脑。当然,对她的评价是褒义还是贬义,完全取决于她每次恋爱的结果。
“可我有些担心……”
訾奶娇说出了她的顾虑,其中有一部分是岑银子刚刚帮她总结的。
“嗨,这有什么好担心的。马上,打电话直接问啊。”
花椒拿起手机递给她,连声催她打电话给纪之。
“算了,都这么晚人家要休息了。”
訾奶娇怎么也不愿意问,也许她害怕听到不好的答案,下意识地在回避风险。
“真没出息。电话号码多少,我来问。”
花椒是个好奇心旺盛的女孩,她把訾奶娇当成知心好友,对她的事件件上心。
“您老歇着吧,行吗?看看你的样子,在外面疯了一天,弄得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的回来,还老揪住我不放,你不累呀?”
訾奶娇把花椒从被炉里拽了起来,推着她往浴室走。
“快去洗澡,一身烟味熏死人了。叫你男朋友快点戒烟吧,不然我可不会让你俩在家里约会,别想干坏事。”
“那你明天记得问他啊。”
花椒从浴室里掏出脑袋说了一句。訾奶娇把她的头按回去,浴室里又响起她五音不全的歌声。
訾奶娇苦笑着摇了摇头,作为一个拥有绝对音感的歌手,每天听着音痴室友荒腔走板的歌声,她的心里像猫抓,既痛苦又无奈。但花椒对訾奶娇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朋友,每当她情绪降到冰点的时候,花椒总陪在她身边,安慰她、鼓励她、逗她开心,让她重新快乐起来。訾奶娇庆幸生命里有岑银子和花椒的出现,这两人的存在就像是她在弹尽粮绝时的能量补给和精神食粮,友情对她而言弥足珍贵。
夜已经很深了,房间里早熄了灯。厚厚的窗帘遮住了户外各种虚弱的光源,黑暗正是夜的本相。訾奶娇和花椒的床并排在一起,枕头也离得很近。两个人都喜欢躺在床上聊天,总有说不完的话,可此刻花椒就躺在訾奶娇枕边,没有一点动静,仿佛和这静谧的黑暗融化在了一起。
她是太累了吧,訾奶娇心想。她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,只有那里反射到不知哪里来的一束光亮。可哪怕只是几点蒙尘的星光,她也将目光停驻在那里,因为她实在不舍得就此睡去。她回味着点滴的甘甜,疯狂幻想着有关纪之的一切,又把他的名字念了几百遍,直到那两个字的咒语最终使她安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