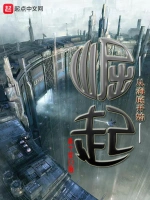从纪之家回来后,訾奶娇一直没找到机会和他好好谈谈。她知道纪之最近忙着新剧的预演,也不愿多做打扰。可她心里总犯嘀咕,担心自己不被他的家人认同。想到两人不明朗的未来,她时不时的伤春悲秋,心底渐渐蒙上爱的阴影。
现实不会姑息某个人爱忧愁的坏毛病,无论欢喜与不欢喜,钱总是要挣的,工作大过天,谁也翻不过天去不是。
訾奶娇的工作时间又到了。她穿过后台的音控室走到台上,撩开幕布瞥了一眼,贵宾席空空如也,其他位子也只有零星几个客人。果然周一是个没人气的日子啊。她叹了口气,对晚上的演出也懒心无肠了。
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,中午的时候艳阳高照,叫人巴不得把长袖截成T恤、长裙截成短裙穿,胳膊和腿定露在外面才感觉到呼吸顺畅;可一早一晚又是冻手冻脚的温度。身体实在太难将息,不经意间清鼻涕、咳嗽、头痛都来了。訾奶娇是个常年不穿袜子的人,所谓“寒从脚起”,她在感冒这件事上从来不落人后。养父母在世时没少说她,以前她都当耳旁风,如今养父母不在了,他们的话訾奶娇倒是常常想起。她抽了抽鼻子,赶紧为自己加上了披风。
訾奶娇看着墙上的时间,七点十五,还早。按照今天这个上座率,八点的首场演出恐怕要延后一小时了。后台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挺悠闲,吃饭的吃饭,聊天的聊天,完全没有平时演出之前的紧张气氛。
这时一个叫久保的女人从音控室走出来,后面跟着另一个和久保同样难以形容的青年人。訾奶娇和久保很熟,是要好的朋友。久保作为女性是非常特别的:高高的个子,肩膀宽阔身材瘦削,脸部特征尤其突出——无论从正面或者侧面看上去,她的脸都像被谁重击了一拳的样子,没有鼻子,嘴唇凸起,加上四方的脸型,确实说不上好看。除了长相男性化,久保说话的声音也比女人粗许多,她走起路来摆副很大,抽烟喝酒的动作比男人还要潇洒豪迈。訾奶娇刚来店里工作的的时候,和谁都不敢敞开聊天,虽然仔细辨认了多次,她仍不能确认久保的性别,又不好意问店里的人。不过久保虽然长得与众不同,但性格却很开朗,待人也热情。訾奶娇渐渐和她熟起来,终于通过一次厕所的偶遇确定了久保的性别。
“小姑娘,一直觉得我是个男的吧?”
那一天,久保弯腰站在洗手池前冲水,她扭头盯着訾奶娇看,一脸坏笑。“没有没有,你误会了……”訾奶娇红着脸想解释,被个性耿直的久保打断了。“没关系啦,大多数人都跟你一样,我又不会往心里去。坦白说,我爸喝醉酒的时候也时常把我当成弟弟呢,还闭着眼叫唤‘臭小子给我拿酒!’很好笑吧?”久保说完爽朗地大笑起来,訾奶娇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朋友。
短发、白衬衫、深色背心和直筒裤,必不可少的领结,是久保日常工作时的打扮,鲜有变化。今天久保打了个红色领结,看上去很奇怪。訾奶娇没见过她用暖色系的装饰,正想过去问一句,一眼望见久保身后那位……怎么说呢?外形同样“雌雄莫辨”的人。“他”留着利落的短发,戴着耳钉,长相和面部扁平的久保相反,额头、鼻子、下巴都十分突兀;一身灰色休闲服,黑白相间的运动鞋,像是刚刚跑步进来的样子。訾奶娇看着“他”和久保眉来眼去神色暧昧,甚至从后面抱住久保的腰,在她耳边吐着烟圈,久保也没有不高兴,反而还对着“他”笑,这实在很奇怪。要知道久保最讨厌别人碰她的腰。“我的腰上都是痒痒肉,不能碰,碰多了我会得面瘫,不停流口水的。”久保曾一本正经的这样说过,店里的人都知道。
訾奶娇听说久保之前交往过三个男朋友,都因为各种理由和她分手了。她每次恋爱都很认真,却总被无情伤害,这导致她的外貌举止越来越趋向男性化,可她的心理究竟是男是女一直是个谜。
“奶娇,楞在那儿干嘛?”久保走过去在訾奶娇额头拍了一掌,“今晚可是陡降了七八度,你怎么又把外套脱了?快点披好。”
久保今晚格外热情,她见訾奶娇的披风快落下去了,连忙帮她披好。訾奶娇见好友如此开心,她也觉得快乐,其他事没那么重要了。
“你好。”
訾奶娇微笑着向“他”点头。
“你好,美丽的小姐。”
“他”也十分绅士的地回答,听起来声线粗犷。果然是个男的吧?訾奶娇心想。她扭头吐了下舌头,正巧被迎面而来的花椒撞上。
“死丫头,冲我做什么鬼脸呢。”
花椒费力地抬起鱼尾裙包裹着的腿,想给訾奶娇屁股上来一脚,可惜没得逞。訾奶娇冲花椒做了个鬼脸,一溜小跑去了更衣室。
訾奶娇推开更衣室的门,不到两秒又给关了回去。她叉着腰叹了口气,再一次打开了房门。房间里烟雾缭绕,本来就瓦数不高的白炽灯,这会儿更加朦胧模糊。
“这是更衣室吗?这是毒气室吧?”
訾奶娇面带不悦,快步走到窗前把几扇窗通通打开。房间里的人几声轻笑,热情地和她打起招呼来。并不宽敞的更衣室里挤了七八个人,包含了罗马尼亚、印度尼西亚、韩国三个国家。她们都是店里的歌舞演员,无一例外的手里拿着烟。看着她们吞云吐雾心满意足的样子,訾奶娇脑海里忽然浮现出鸦片战争时期那些人抽大烟的画面。虽然抽烟和抽大烟不是一回事,但在密闭的空间里抽烟着实让人讨厌。
訾奶娇从更衣室的柜子里拿出自己的毛衣,凑在鼻子前闻了下,还好没有烟味。这时艾娅走了过来,她是个印尼女孩儿。
“娇,你的男人不抽烟吗?”
艾娅皮肤黝黑,身材性感,踩着十公分的高跟鞋,穿着短到大腿根的横条纹包臀裙,胸有一半露在外面。她用细长的手指夾着香烟,烟圈从她厚厚的嘴唇吐了出来,她眯着眼噘着嘴,好像到了极乐世界。訾奶娇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,害怕烟味沾到自己身上。“对不起啊,娇,我忘了你不喜欢闻烟味。”艾娅连忙用手挥舞了几下,猩红的指甲格外刺眼。“没关系。”訾奶娇勉强笑了笑。“娇,你的男人抽烟吗?”艾娅又问了一遍,她歪头看着訾奶娇,似乎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。
訾奶娇不太喜欢艾娅总用“你的男人”来称呼纪之。明明两人还在热恋中,被她说的像老夫老妻似的。她认为恋爱中每一个阶段的身份带来的快乐都应该被充分享受,她现在是纪之的女朋友,将来会是纪之的未婚妻、纪之的妻子。她更希望在若干年后躺进坟墓的时候,她的名字和纪之刻到一起。
“我男朋友从来不抽烟。他叫纪之。”
訾奶娇细声细气地说。她觉得有必要提醒艾娅注意,纪之是有名字的,他现在还不是自己的丈夫。
“哦,真的吗?那你的男人太与众不同了,呃…我的意思是他非常优秀,懂得克制自己。”
艾娅眼睛瞪得溜圆,故作夸张地说道。她说话的时候腰肢乱摆,手舞足蹈,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都配合了相应的表情。她是个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特别丰富的人。在訾奶娇的眼里艾娅不仅是个舞者,而且是个绝好的演员,只让她跳舞实在太屈才了。艾娅固执地称纪之为“你的男人”,訾奶娇哭笑不得,只能听之任之了。
周一的生意果然惨淡,原本每晚的三场演出减至两场,下班的时间也提前了十分钟。生意不好会让老板烦恼,但女孩子们却格外轻松。訾奶娇和女孩儿们说说笑笑地回到宿舍。虽然是国外临时的家,可也是个让人感到温馨和亲切的地方。
訾奶娇住的宿舍楼是间两层楼的木屋,和演出地只隔了几栋楼,步行只需一两分钟。房子外层别出心裁地刷了雪白色、绘了花里胡哨的画,还在二楼顶上挂了个牌子,上面写着“桃子屋”三个字,字的上面一个硕大的粉红色桃子圆鼓鼓胖嘟嘟的,看了让人嘴馋。从街头一眼望到街尾,“桃子屋”如同夹杂在多副素描画之中的彩色景物画,格外引人注目。
“桃子屋”是专供店里的外籍演员居住的地方,里面还算宽敞,楼下楼下共有八个房间,厨房、浴室和卫生间都在一楼,大家共同使用。店里的中国籍演员最受欢迎,因此招募得多些,全部安排在二楼;而一楼五间房则住了罗马尼亚、印尼、韩国、印度等几个国家的女孩儿。“桃子屋”说小不小,说大不大,竟然住下了二十多个年轻女孩儿。每到深夜,“桃子屋”就变成了女生澡堂,可谓画风绮丽、美景无数。这里几乎每个人都不会穿长袖长裤的睡衣,清一色全是吊带裸胸短到大腿的真丝睡裙。那是当年的时尚。起先一个女孩这么穿,同寝室的觉得好看就学起来,慢慢隔壁寝室的、别国的、楼上的,大家通通这样穿起来。一两点钟的夜里,“桃子屋”里灯火通明,穿着五颜六色性感睡衣的妙龄女子,披着头发半露酥胸,皮肤无论黑白或黄,都泛着青春的光泽;她们有许多都不穿鞋,光着脚踩在木地板上,楼下楼下地串门,在唯一的浴室和厕所之间进进出出,厨房里奏起锅碗瓢盆的交响乐……那画面,栩栩然一副活色生香的浮世绘百花图。
訾奶娇和她的同事们在“桃子屋”住了几个月时间,彼此相处融洽、互助互爱,虽然偶有小摩擦,但从没发生过大的矛盾。訾奶娇和朋友们都很喜欢这里,工作之余,“桃子屋”就是天堂和乐园了。周一是一周里最平淡的日子,工作时大家都意兴阑珊,但只要一回到“桃子屋”,女孩们立刻变得兴致高昂,睡衣晚会如常开始……可这天却发生了一件让大家始料未及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