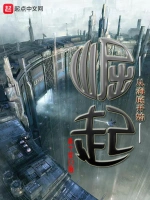天照山度假屋的离奇事件过去两天后,訾奶娇接到纪之的电话,听到一个令她震惊万分的消息――杀人凶手是景的龙凤胎儿女。訾奶娇怀疑自己的耳朵,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。她感到讶异、心痛,还有种对残酷现实无能为力的愤怒。
“喂,奶娇,你在听吗?”
电话那头纪之关切地询问,她回过神来答应了一句。
“晚上我来接你。”
纪之说完匆匆挂了电话。
訾奶娇的心郁结难抒,于是站到窗边做深呼吸。城市里的雪早化得无影无踪,树木的轮廓清晰突显,地面被清扫得干干净净,往上看去万里晴空一碧如洗。天空宛如倒悬的深海,偶尔飘过的浮云好似海里蜿游的鱼,慢慢悠悠忽隐忽现。此情此景让訾奶娇心里生出许多感慨——世间万物,只有人是不洁的。花草树木、山川河流、星辰大海、浩渺宇宙,大自然里古老、原始的都美好纯净,它们是真正的主人;再看那些活着的东西(据说他们有思想),动物们也受丛林法则的约束,唯有人心不守规矩,总是出卖本性,爱与魔鬼做交易。人类是地球上最大的污染源。
想着想着,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偏激,于是厌恶地皱起眉头,好像在和自己生气。她偶尔会反对自己的某些思想,却永远忠诚于自己的心。
彼时,窗外的美景在她眼里不过是一副定格的画,那些流动的光影难以牵动她的眼神。她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,脑海里全是雪。天照山的大雪在她心里持续下着,雪地里埋着的女尸浮现在眼前。女人死去的样子唯美动人,訾奶娇并不觉得可怕,她执着的以为那女人就是爱情的祭品,因此格外伤感。
女人多数是被爱情左右的动物,明明一整天都在为悲剧叹息,可见到爱人那一刻她又进入了喜剧的角色。她抱着一兜必要的随身用品,欢快得像只小鹿。她动作敏捷地跳上纪之的车,心情既有去天照山时少女怀春般的喜悦,又有小学生和最好的伙伴出游时的兴奋。
“很开心吗?”纪之握着方向盘,余光温柔地投向她欣喜的脸。
“嗯!”
她用力地点头,亮晶晶的大眼睛里闪烁着爱笑的星星。
纪之为了她决定从家里搬出来住,就在离“桃子屋”不远的“花塔路”租了个小套间,今晚正式把她接过去。她没想到纪之办事效率这么高,埋怨自己东西没带齐。
“从明天起,我每晚都来接你下班。白天你愿意待在家里或者回桃子屋都可以,随你。今晚东西带少了没关系的,可以每天回去拿一点。”
纪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,好像从不为任何事着急。他的言行举止极其自律,整个人像一部精密的仪器,从不会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。訾奶娇对他崇拜已极。她有时甚至会想,宁愿自己变成惹人厌的苍耳,紧紧吸附在纪之身上,无论如何也不离开。
訾奶娇走进新家,立刻就爱上了它,就像前几天刚见到天照山的小木屋时一样,这间房子让她倍感亲切。因为这里是她和纪之的家。她的心情好像浮舟靠了岸,风急雨骤的日子已是遥远的回忆。
新房子有两室一厅,面积大小合适,客厅包含一个开放式的厨房;卧室温馨别致,小阳台尤其让她惊喜;纪之客卧改成了书房,方便他在家工作。虽然是租房,可房子里家具都是全新的,窗帘的颜色也特地选了她喜欢的。这间房子的一切都让她无可挑剔,堪称完美。
訾奶娇欢呼着扑倒在纪之的怀里,高兴地用脑袋使劲在他胸前拱来拱去,活像只西瓜地里的猹。纪之被她逗得哈哈大笑,用十指穿过她的头发,像捧祭品那样捧着她的头,张大嘴巴假装要一口把她吃掉。訾奶娇使劲晃动着脑袋不肯就范,她用力往上一蹦,出其不意地在他鼻子上咬了一口,然后奋力挣脱了他的怀抱,逃得比泥鳅还溜撒。纪之捂着鼻子哭笑不得,威胁要把她的恶作剧写进剧本里。
“我做饭给你吃吧。”
两人玩儿累了,訾奶娇说她要试着履行主妇的职责。她叉腰站在厨房,用王者的姿态扫视了一圈,惊奇地发现发现厨房用具一应俱全,每件物品都合她的心意。
“纪之,这些东西都是你买的?你可不像熟悉厨房的人啊。”“当然是我买的,不过同事们也帮了点小忙。怎样,还称心吗?”“嗯!”
訾奶娇满心欢喜地操持起来。她曾经认为围着丈夫和家庭打转的主妇是堕落的,那时她的心很野,很大。不过短短几年,她的心境转变了,她渴望爱情和家庭的温暖,以前看来卑微的事如今在她眼里是伟大的,甚至还有种神圣感。如今她是唯爱论的忠实拥趸,她认为爱情的价值超越这世上所有的奇珍异宝。
纪之坐在沙发上看棒球比赛,訾奶娇对球类运动一窍不通,也不感兴趣,不过她很享受站在厨房岛台前为心爱的人做料理。她希望无论他做什么都可以,只要在她目光之所及。
訾奶娇熟练地切着黄瓜丝,切了一截儿后才发现自忘了给黄瓜刮皮。不刮皮也可以吧?她记得小时候养父总给她啃不刮皮的小黄瓜。想起养父她心里痛了一下。她稍作停顿,继续切那根没刮皮的黄瓜。
“宵夜来了。”訾奶娇端着一大盘蔬菜莎放到纪之面前。“吃这么素吗?你喂兔子呢。”纪之看到整盘都是花花绿绿的菜提出了抗议。“这是宵夜,又不是正餐,吃那么多肉一会儿睡觉会做噩梦的。”
两人新家的第一餐是如此环保和仁慈。不过她这时意识到宵夜吃沙拉或许是件奇怪的事。她见纪之嘴上抗议,实际行动却很照顾她的感受——他没有挑剔黄瓜不去皮、土豆不太软的问题,吃得十分享受。訾奶娇心里暗下决定,哪怕还不是真正的妻子,也要像妻子那样去了解和照顾丈夫。至少得给他做顿像样的饭菜啊,她想。
“纪之,你白天在电话里说的话,是真的吗?”訾奶娇还是放不下天照山那件事。“我也不敢相信,竟然是两个五六岁的孩子干的。”纪之面色凝重地和她说起了事情的详细经过。
事发当晚八点半,景的两个孩子炒着要吃碳烤酸奶,夫妻俩被闹得实在没办法,于是景开车去山下超市买。因为景的丈夫以前出过交通事故,还没重新拿到驾照,所以由他在家照顾孩子。景走了之后没多久,丈夫接到了死者的电话,约他立刻出去见面。景的丈夫担心妻子回来撞见,于是匆匆出门赴约。
“等一下,这么说来,那个叫黑雪的女人和景的丈夫双双出轨了?”
訾奶娇越听越觉得离谱。
“是啊,听说黑雪的婚期原本就在下月,很近了。景和她丈夫结婚十年,丈夫是个美男子,因为穷才入赘到景家的。看吧,典型的女强男弱的婚姻,所以两人一直是貌合神离的。”
纪之继续叙述。
黑雪和景的丈夫在大雪中谈了十多分钟,最终没有谈拢。黑雪要求景的丈夫离婚,自己也会取消婚约和他在一起,可景的丈夫死活不同意。
“本来是个老套的三角恋故事,可结局太让人意外了。景的丈夫不想和黑雪纠缠,于是把她一个人扔在大雪里就回屋了。回去之后觉得心烦,就把卧室的音响打开听音乐。两个孩子在客厅玩游戏,他也没心思去管。”
“结果两个孩子开门出去,他因为开着音乐所以没听见?”
訾奶娇问。
“是的,但让人没想到的是,其实那两个孩子早就发现爸爸和另一个女人的关系,两人搂抱和亲吻他们都看到过。只是孩子太小,对那些事不太懂,但他们心里是非常厌恶黑雪的。”
“所以他们动手把黑雪给……杀了?我的天,怎么可能!”
訾奶娇整个身心都在抗拒这个荒谬的故事。
“和你想象的有些不同。两个孩子跑出去以后见到还在原地哭泣的黑雪,那时黑雪是背对着他们的。兄妹俩知道黑雪又来找他们的爸爸十分气愤,所以用小孩子表达愤怒的方式做了不好的事情。”
纪之说起这段时一直皱着眉头,他的心里也是接受不了的。
“什么事?他们怎么做的?”
訾奶娇连忙追问。
“两个孩子一人捡了一块石头,朝黑雪的背后砸去。很不凑巧,两块石头都砸中了黑雪的后脑。黑雪叫了一声就倒下去了。其实当时她只是昏迷,及时施救或许还有救……唉!两个孩子对‘死亡’这件事没有多少概念,但看到黑雪倒地不动还是吓到了,所以两人赶紧跑回家里躲起来。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样任由黑雪留在雪地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”
听着听着,訾奶娇撑在暖桌上的手越放越低,后来干脆整个下巴磕到桌子上,两手伸直了握着水杯。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茶杯,发出一声低叹。
“奶娇,你这是干嘛,练瑜伽呢?”
纪之见她跪在地上撅着屁股塌着腰,整个上半身趴在暖桌上,对着一杯茶傻傻地叹气,不觉好笑。他伸手捏住她的鼻子,她也不挣扎,顺势去啃他的手掌。他呵呵地笑着,像抱婴儿一样把她抱进怀里。
“纪之,黑雪就这样死了?那她是什么时候被景的丈夫发现的?她身上的衣服呢?”
她靠在纪之的怀里,想到黑雪倏然面露忧伤。
“景的丈夫说景离开后大约一小时,孩子们追着问他妈妈怎么还不回,他到门外等了几分钟,没等到妻子回来,又想起留在雪中的黑雪,于是回到原处一看……”
纪之随后发表了一番简短的感慨,訾奶娇觉得那些话不如他的心跳好听。他的心跳强劲有力、节奏均匀,带有镇静剂的功效。自从天照山的事之后,她时常感到患得患失。她的脑海里偶尔会出现一些可怕的画面:有时是黑雪的脸变成了自己的;有时是纪之伤心欲绝地痛哭着,眼里流出了血;有时是纪之抱着自己坐在柿子树下,两人冻成了两具僵硬的尸体……这些画面她从没有刻意去想象过,它们毫无征兆地占据了她的脑,她拼命抗拒心底的恐惧也无法让那些画面消失。这些事她对纪之绝口不提,因为每当纪之皱着眉头忧心忡忡看着她,他的眼神总是刺痛她的心。
“奶娇,你在听吗?”
纪之摇动着她的身体。
“哦,听着呢。”
“真是的,你要我说给你听的,可我边说你边走神,脑子到底在想什么?嗯?”
纪之低下头,认真地看着她的脸,就动物学家研究动物那样。訾奶娇鼓起腮帮,“噗噗”地怪笑着。她知道纪之喜欢小动物,自己就演个有趣的青蛙给他看。
“你接着说,景的丈夫回到原处看见什么了?”
她又问。
“当然是躺在地上的黑雪啊。他以为黑雪死了,吓得魂飞魄散。其实他并没有认真查看,或许黑雪当时还没断气呢。”
“后来呢?他就把黑雪埋在雪里了?”
黑雪埋在雪里的景象刻在了訾奶娇的脑海里,她有时会恍惚地以为黑雪是代替自己一语成谶了。她总爱把别人的悲剧叠加到自己身上,好像穿了一件不适合的衣服,非但不能悦己,反而会令自己深陷悲伤的囹圄。
“是啊,当时黑雪穿着睡袍和外套,看来也是匆匆从家里跑出来的。那两件衣服是景的丈夫买给她的,和景的衣服同款。景的丈夫害怕尸体被发现后妻子看到黑雪的衣服起疑,所以就给她脱掉了。”
“那内衣裤呢和鞋袜呢?为什么也脱了?”
“据他自己交代,他爱黑雪的身体,他说她一丝不挂的时候是最美的,所以才那样做。他说当时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,还说‘怕她冷,就用雪为她穿起衣裳吧。’他就是个变态,你不觉得吗?”
訾奶娇点头表示赞同纪之的话。
“那为什么不把她整个儿埋起来?哦,是不是景的丈夫听到有人来了,所以匆忙之中没有把黑雪埋好?”
“真聪明。景的丈夫埋尸的时候听到车响,知道那个时间还在山里开车的一定是自己的妻子,所以什么也顾不上就逃回去了。”
“他大概还是爱她的吧?”
沉默许久,訾奶娇无不惋惜地说道。
“何以见得?”
“景不是说他的丈夫清晨听到狼叫,出门去看过吗?他一定是去看黑雪吧,也许会跪在她面前哭泣,祈求她的原谅。”
“哦,是吗……”
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。訾奶娇尽量尝试用听故事而不是听事故的心态去了解这样事,但当她得知全貌后仍然难以控制地陷入到悲伤的情绪之中。
黑雪的死对纪之来说只是个意外事件,他的情绪丝毫不受影响,还期待着下次再带她去天照山度假。他说起黑雪的时候那样不在乎,好像她只是天照山里冻死的一只鸟。
訾奶娇不觉得纪之无情,她反而更加渴望依附在他身上。她眼里的纪之是个与寒冷和阴暗绝缘的生物,只要在他身边,就仿佛时刻沐浴在阳光之下,她能闻到“永恒”的味道。
对訾奶娇来说,一年四季都有让她感到孤独的时刻。生机盎然的春天最没有孤独的理由,可无人共赏桃花就是孤独的理由;秋天颜色饱满,季节浪漫,孤独的理由就是她的琴弦断了又不愿续上;夏天炎热漫长,孤独的理由是那温热的江水夺去她的挚爱,把她的心冻伤至残;冬天是一个每天都可以任意孤独的季节,寂寞无处不在……可只要有了纪之,他将终结一切孤独。
纪之此刻用行动在告诉她:傻瓜才在心里盛满悲伤,才让身体里流淌着孤独的余毒,他要帮她把那些可恶的东西通通排出去。
纪之贴在她的耳边说着情话,他的唇温热湿润,他的皮肤像浸了木头、竹叶和蕨类植物的香料,由内而外散发着一股异常吸引人的味道。她吸气的时候身体随之起伏,暖光之下如同移动变幻着的沙丘,曼妙神秘让人沉迷。他炙烈的情感潮水般向她倾泻,他在巨浪的巅峰处主宰着潮汐,她好像被她的“神”重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,整个人宛如新生。
天照山的寒冷和悲凉就这样被他推到了过去,她希望她和纪之永远不会成为类似悲剧的男女主角——她在心里默默祈求了一万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