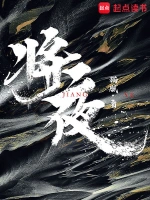不多时一位英武青年掀开帐门大步走了进来,向着背对帐门沉思的拓跋昊抱拳行礼:“野利闵参见父皇!”
野利闵乃是他的次女夫婿,如今执掌禁卫军,也即是拓跋昊手头最精锐的骑兵统领。
“驸马,朕来问你,你安排了何人在前面统领两千骑兵?此前不过千余汉骑出城,此人竟然仍由汉骑猖獗,难道是畏战不前?”
拓跋昊的话语中隐含怒气,攻城部队的溃退在他看来,比不得寄托有自己重望的骑兵不敢出战更为让他生气。
野利闵不慌不忙地回答:“父皇息怒,此事容儿臣分解。”
“于前线统领骑兵之人,正是儿臣副将,父皇也极为了解的仁多唆甲将军。仁多将军骁勇善战,绝非畏战不前之人,儿臣也派人去询问原因去了,想来要不了多久便能有消息传来,还请父皇暂且息怒。”
野利闵的解释果然有用,听说骑兵乃是由仁多唆甲统领之后,拓跋昊脸上的怒色迅速消退,显然是对这仁多唆甲也是异常信任。
他来回踱了几步,回身对野利闵道:“在这账中呆得气闷,你陪朕出去走走。”
帐外寒冷的空气让拓跋昊精神为之一振,感受着北风的呼啸,他用力揉了揉脸颊,长长呼出一口白雾,看着北方湛蓝的天空叹道:“天气越来越冷,这两日还好,再过几次,大雪可能说下便下,到时候我军无论运粮、取暖,还是攻城都将更为困难,奈之若何?”
野利闵从身后给他披上一件虎皮大氅,回答道:“父皇过虑了。我军十数万精锐之师,纵遇一时挫折,那龙州城也指日可下。儿臣前日寻了两名山中打猎的猎户询问过,这等天气,至少七、八日内当不会下雪,算来我军时间也尚还充裕。”
“更何况还有嵬名浪老将军负责统筹全局,对上欠缺统兵精力的夏松老儿,儿臣看不出有何需要担忧的。”
或许是野利闵的从容镇定感染了他,又或许是父子数十年的筹划给他的底气,拓跋号脸上总算露出了一丝笑容。他吩咐侍卫道:“去,给朕牵马来!朕许久未曾纵马狂奔了,今日要学那苏学士,也来个老夫聊发少年狂!”
那侍卫不敢应下,偷偷望向野利闵,被拓跋昊一脚踢在腿上:“怎的,朕还使唤不动你了?”
野利闵斥责那侍卫:“还不去快牵马来?陛下只在这营中消遣,又不外出,你这般拖沓作甚!”又对拓跋昊道:“父皇,如今两军阵前交锋,又有大队汉骑在我身后出没,儿臣也认为实在不宜外出,不如儿臣陪父皇就在这营中散散步。儿臣对后续战事有些想法,正要向父皇禀告。”
那侍卫又朝拓跋昊看了一眼,见自家主子不再恶狠狠地瞪着他,立刻不声不响地退到了后面。
“也罢!你们啊,便是想要朕这也不做,那也不做,哪里都不去才能合了你们的心思。”
“说罢小子,你有何想法,说来让朕听听!若是朕不满意了,当心抽你鞭子。”
拓跋昊并未因被阻拦而生气,反倒是迈开大步向前行去,野利闵紧紧跟在他身后,惶恐道:“儿臣答错要挨鞭子,不知父皇若是满意了,又会如何赏赐儿臣?”
“哈哈哈……你啊,跟宁玉成婚才两年罢?怎的将她的古灵精怪都学会了?若是朕满意了,你想要什么赏赐啊?”
“父皇,若是儿臣的回答让父皇满意,还请父皇允许让儿臣参与对汉军的进攻,麾下骑兵可由闻喜兄长暂领,儿臣只盼能上阵亲手杀敌即可。”野利闵趁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。叔父野利顺被汉军击败,到如今生死不知,他这侄儿自然要为叔父报仇。
“不可,此事朕不会答允你的。朕教了你多少次,为将者,不可将眼光囿于一隅。朕知晓你欲为你叔父报仇,可报仇的方式并非只有逞匹夫之勇、亲手上阵杀敌一种。我大秦不缺冲锋陷阵的猛将,缺的是如同元帅一般能统筹全局的大将,与你一般自幼聪慧之人不少,但能与你一样沉稳之人却是不多,这也是朕看重你的原因,希望你能早日成长起来,成为为朝廷独挡一面之大将才是。”
野利闵沉默了一会,还是回答道:“儿臣其实并非仅只是为三叔报仇,也是想亲身体验一番战阵厮杀的紧张和激烈。儿臣听闻,未曾经历过真正战阵之人,哪怕他武艺再如何高强,心性再如何沉稳,与亲自上阵搏杀百战余生的勇士相比也是大有不如,因此……”
野利闵的回答大出拓跋昊的意料,他停住了脚步回过身来:“如此说来,你想上阵厮杀是因为想锤炼自己的心性?”
野利闵迎着拓跋昊的眼神,说话掷地有声:“儿臣确有此意,还请父皇恩准!”
拓跋昊沉默不语,转身继续向前走去,野利闵也默默跟上,心下忐忑不定,不知自己的回答是否会惹恼于他。
走了十余步,拓跋昊悠然叹道:“年轻真是好啊,如此亦可,明日你去元帅那里点卯,便让麻夏与黑利二人随你左右,也可护你平安。”
野利闵大喜过望,拓跋昊不光答允了他的请求,还让自己的两名贴身护卫随自己一同上阵,这真是对自己非同一般的赏识。他立刻向后退了一步,恭敬行礼道:“儿臣多谢父皇!”
这一声谢恩却是语音哽咽。那麻夏与黑利二人均有万夫不当之勇,从来都只护卫在拓跋昊身边须臾不会离开,此刻为了自己的安全,竟然让他二人随自己上阵,可见在这位父皇心中,自己真是如他所言,不是一般的赏识。
拓跋昊又轻声道:“回头你若是有了余暇,多和腾哥儿亲近一些,他性子拗,你这当姐夫的要多也要多管教管教他。”
这是……这是在给自己的未来铺路,野利闵感激涕零,当即伏拜在地:“儿臣……儿臣定不负父皇重托!”
拓跋昊两女两子,长女在七岁时夭折,次女便是嫁给野利闵的宁玉公主,长子拓跋腾比他二姐要小上两岁,如今正是人憎狗嫌的年纪,幼子拓跋定如今才三岁。这天下无论是项人还是汉人、金人的传统,家产都是长子继承制,也即是说,若无意外,拓跋腾便是日后大秦的太子,下一任大秦之主。
拓跋昊自幼缺乏父爱,却不愿自己的儿女再有如同自己一般的经历,对三个孩子十分疼爱,如今更是让他与拓跋腾亲近一些,这其中蕴含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确,这让也是自幼失怙的野利闵如何不感动?
拓跋昊转过身子皱眉道:“你是朕的爱婿,都是一家人,如何行此大礼?快快起身来!”
野利闵闻言连忙爬起,衣袖不经意间将眼角的湿润擦拭了一下,又亦步亦趋地跟在拓跋昊身后。
“不过朕答允你到前线去也是有条件的。”
野利闵等了半晌没有等到下文,当即疑惑道:“父皇又何要求?儿臣一定无有不从。”
“嗯?你自己适才说的,如何忘记得如此干净!”拓跋昊的声音似笑非笑,野利闵微一凝神,这才明白他说的是适才为了替那侍卫解围,自己说是对战事有些想法。
他虽是匆忙之策,好在确实并非信口开河,当下胸有成竹地将自己的想法道了出来。
“父皇,昨日与前日,儿臣曾抽空到前线去看了看龙州的城防……”
“唔,未曾禀报于朕便擅离职守,朕先给你记着。”
“父皇……儿臣知错……”野利闵满头大汗,怎么一不小心就说漏了嘴呢?
好在拓跋昊并非真的要与他计较,他虽然心中暗骂自己愚蠢,却也不是那么慌张,定了定神后继续道:“儿臣虽然隔得很远,亦能看出龙州城的防御被夏松老儿作了极大修改,城头搭建了木顶,以至于我军的投石车对布置在城头汉军几无威胁,只能对城墙造成有限伤害。”
“除此之外,今日儿臣派出观战的士兵回来禀告,说是能看见汉军在城内修建了十余座高塔,弓箭手可以在其上居高临下对我军攻城部队进行打击,这也是上午我军进攻不利的一个原因。”
“儿臣以为,时间不利于我军,要争取时间,便须得有所舍弃。投石车距离太远,一则对汉军的打击精度不够,二则射程太短,不能摧毁掉汉军的高塔。因此儿臣建议,投石车当向前抵近龙州,哪怕进入汉军床弩的射程之内也无妨,便是要和他们拼这个消耗!投石车修复易,弩车修复难,我军兵力又胜于汉军数倍,这样的消耗我军能承受,而汉军必然不能。”
“此外,为了防备城中汉骑突袭,我军当充分利用兵力优势,在战场上大肆挖掘壕沟,或是陷马坑;我军身后亦可如此,这也是逼迫潜伏的汉骑主动进攻的打草惊蛇之策!”
“想必汉骑也无法坐视我军挖好壕沟,否则他们的威慑便将失去。无论汉骑主动进攻,或是我军挖好沟渠,最终的种结果都可让我军使出全力用于攻取龙州城上。”